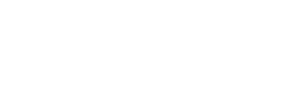【香港國際舞蹈影像節 2022】開幕節目 「此地此身」:身體作為存檔
文: 俞若玫

身體微妙,可知也未知,不只是修辭上的譬喻,也是分秒發揮有機功能,同時,包納吐隔慾望、回憶、情感、禁制、潛意識,是自我和他者的第一道門戶,一場至死方休的生成及變化場域。總覺得,身體洞口、痛點、疤痕、皺窩、炎症、瘀黑、腫塊,都是特定時間及空間的存活信息,如翻開自我及時代的紀錄,內顯的不是數字及事件,而是經歷了時間訓練的想要和不再想要,能和不能的挑戰、若即若離的回憶、抵抗和服從的成績表、煩厭和甜順的總和。
後殖及性別研究學者辛格(Julietta Singh)在《沒有存檔會修復你》(No Archive Will Restore You)一書,有如此美麗的形容(大意譯為):「身體存檔是一場調較,一次有希望的集結,一場抗拒理性強拍的愛的行動。它是一種對自我—身體作為生成及脫離的認知方法,同時抓混時間及物事,走近而不是抵抗自我。」[1]
我參考她的角度去欣賞今次跳格的「此地此身」四個作品。四位女創作人翻展身體內內外外,從跳到不跳,從這裡到那裡,從詩化的、美學的、非因果的、斷裂的影像去再現別人的,體現自己的、世界的陣痛及流變。
先說陳巧真的《失去的部份》,它似是一首辯證失去和存有的影像詩。導演的跳接速度及方法,似漫不經心又自覺,不著力但內沉,情感濃度是身體感應以後的痛。乾枯縮捲的葉子,沙沙作響,是死亡絕響還是另一種維度的再生? 同樣皺褶的大腦,神經元小了,又有沒有另一種非理性的靈性存在? 她以詩化的影像,微觀他者身體的孔洞,從偶發遇上掙扎抽搐的蜜蜂到定鏡一場脫牙吐血,還有水道內似迷了路又似轉出路的婉婉水蛇,都讓我想起台灣女詩人夏宇的名句: 「拔掉了還疼,一種空洞的疼」,失去才讓存在變得無比真實,彷彿對城市的愛。一場無盡的雨。斷過的沒有斷過的手。回到街上。停下來。抑鬱可能是保護色。回到地鐡,看得見的生活速度。一段段回到正常秩序的幻影。如果有。最後。一場釋放的舞動。又或只有一個方向的未來? 那把強擋巨風的傘。
張紫茵作品《自如身》(英文名字是有趣地從負面說的If I Can’t dance)視點也在受傷的舞者,敘事性較強,導演自身的經歷、創作過程的感遇跟不同受傷舞者的經驗並置。 另,在工廈擺拍曾受傷的舞者莫嫣(Jennifer),再現一場舞者跟自己角力的痛和快。好看是,舞者和兩個自己共舞:回憶中的我,當下正在以身體思考的我 ; 還有,被要求的我和對自己要求的我。如果能夠更深入Jennifer 這位在香港選擇以獨立身份創作的舞者,對她的舞蹈訓練、身體經歷以及社會脈絡有更細緻的深領,打開她的痛,她的無眠的情感向度,可能更能引起大家的共感。其他舞者的說話也不需煩雜成為補足的資料。也期待導演的身影在進出之間,並疊之時,飄落生根,有更強的情感連結,如果能讓不同身體及酷兒身份重疊於主流以外的時空,互相看見,相視而舞,自如地跳,很是美。
葉奕蕾作品《海坐下來時沒有風 》是自述的流動影像私書寫。時光明媚,風起時,在路上,年輕舞者一個人的身影進入/離開、開始/結束、痕跡/消逝、休息/探奇、路上/停留,遺忘/難忘,歲月和生命在過渡中慢慢前行。職業舞者的舞台框架,創作人的鏡頭框架,病人的醫院窗框,因為一場意外,重置在一起。二十年前的經歷。好像回過來再次召手。身份的轉移。一個人的風景。沒有風。漸漸成為一班人的浪漫和笑語。無人的排舞室如漸涼的黃昏。舞團場地被鐺鐺有聲如當權者的催趕下清拆。解體。重設。人仍繼續走。在流離。在發夢。在見證。海還未坐下。
莫頌靈作品《180°.78°14’n 15°36’e.2013》很有趣,視點跟其他三個作品完全不一樣,沒有傷口,沒有回憶,連身體也沒有,卻在延展觀眾的眼睛,從右至左一百八十度的定格平移,讓大家沉潛在接近北極的冰川冷石,荒原寒船,在一個獵殺遊戲的設計內,得到意外的平衡、沉靜及療癒。她在。我們都在。亂世下,一起在極北冷境緩慢移動和思考,從自然的身體得到力量及慰藉。
四個作品,四種影像敘事風格,共通的是碎碎私語,詩意地打開時間及身體缺口,在非線性的跳接裡,觀眾能夠以自己的想像縫合不同主體的生成及變化,更接近而不是遠離此時此刻的世界和他者。
跳格──香港國際舞蹈影像節 2022
開幕節目 「此地此身」(世界首映)
導演:張紫茵、陳巧真、莫頌靈、葉奕蕾
放映及購票詳情:https://qrs.ly/yre146i
[1] 原文:“The body as an archive is an attunement, a hopeful gathering, an act of love against the foreclosures of reason. It is a way of knowing the body-self as a becoming and unbecoming thing, of scrambling time and matter, of turning toward rather than against oneself.” (SINGH, 2018, p. 29)